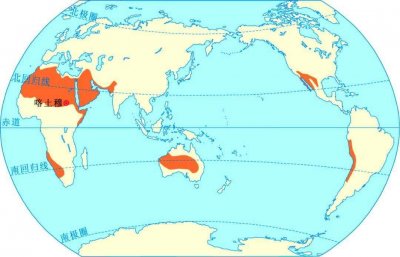宣城记忆之十四:宣城的先贤祠和乡贤祠

十四、宣城的先贤祠和乡贤祠
邢少山
宣城古代有先贤祠和乡贤祠,在这些祠里供奉着历史上在宣城较有名气的政治家,或文人雅士。不过,这两种祠供奉的人物在籍贯有所不同。乡贤祠供奉的完全是本乡本土的人物,而先贤祠则可能是外籍贤能之辈。下面,我分开来说说。

宣城先贤祠,据史志记载:位于敬亭山翠云庵的后面,原叫“五贤祠”, 这五位贤人是谢朓、李白、韩愈、晏殊、范仲庵。祠为徽派砖木三开间抱合式结构,设天井、石雕栏杆,中按假山配置,正厅内典祀五贤人半身塑像。到了清朝,“庙貌寖颓,雀鼠穿穴,蔓滋虫篆,几筵仅存。”(清•佟赋伟《重修敬亭山七贤祠记,下同) 当时的清康熙年间的宁国知府佟赋伟,感慨此祠破败,需要重修,于是他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重修。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纷给响应,捐资献工,于是此祠三个月就修成功了。此祠修得很壮观,“榱桷顿新,馨香增肃。”五贤祠里又增添两人进去,他们是张慎言、姜埰二人,五贤祠变成了七贤祠,人们非常高兴,感叹说:“七贤有知,其欣欣而乐康也!”

大概又过了一百多年,到了道光年间,七贤祠经风吹雨打,又有损坏,知县王成璐看到这情形,认为应该修葺,于是在他的努力下,把七贤又修葺整饬。这时,一户施姓族人还助祀田三十余亩,帮助整建为十数间浅房。这样,先贤祠右侧又建一幢为佛庙,左侧为客堂,再左为“龙宫”,并又增添梅尧臣、施闰章、梅文鼎三人的雕像,七贤祠变成了“十贤祠” 。宣城人经常说的“十贤祠” ,也由此而来。后来,又扩展到十四人。
从五人到十四人,这些先贤大多是宣城人耳熟能详的人物,其人其事多有传扬,其诗其文也多有讽诵,而唯有张慎言和姜埰两人,一直不为人们熟知,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张慎言(1577-1644年),字金铭,山西泽州阳城人,明代思想家、诗人、一品重臣。他能诗能文,为学颇有见地。张慎言提出“可仿而行”,并实施上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五种不同的耕种方法,以促进农业的发展。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1644年4月),明都京师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五月,福王又立于南京,并任张慎言理部事。张晚年漂泊,后流落到宣城,而他对宣城很有感情,尤其对宣城的文脉、风景非常赞赏,他曾有《敬亭睛雨》诗曰: “雨寄睛好尽人知,却喜将晴乍雨时。风气欲侵风更转,倦六半压岫如欹。情文殊愧酬元宰,天地居然是幻师。林杪浮烟烟际阁,有人依阁也何思。”张慎后来身患背疽,拒绝医治,以表殉国,终年六十九岁。宣城人为纪念他对宣城的情义,把他逐参宋典祀敬亭山七贤祠中。

姜埰(1607—1673)明末清初学者。字如农,山东莱阳人。他号称敬亭山人、宣州老兵,与弟姜垓明亡后居吴下以遗民终。他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入为礼部主事,选授礼科给事中。他弹劾权贵,受廷杖入狱,后谪戍宣城卫。他虽遭贬,却非常满意,“垂死承恩淀谴,天威咫尺间。荷戈荒徼去,收骨瘴江边。哀职犹思补,龙髯竟绝攀。桥陵千滴汨,犹在敬亭山”(《赴戌宣州》)。北都先后为李自成军、清军攻破,公乃移家江南,于是他数次往返于南北之间,此间,他写下多首与宣城有关及怀念宣城的诗文。他途徙漂泊有三十年,姜埰始终未忘履行谪戌宣州的使命,可见他对宣城的感情如此深厚。康熙6年(1667)年,已经花甲之年的姜埰携子来宣城,并与当时的复社泰斗、海内遗老沈寿民及吴肃公、沈泌等啸聚敬亭。在此期间,他提笔写下了“自是衰年应埋骨,已促好友为僦舍”的诗句,表明了自己终老归葬的心迹。他又和“海内三遗民”之一沈寿民的相聚,两位遗老同食并卧,姜埰即兴写下了“吾爱沈夫子,应为千里行,何当栖隐处,一饱露葵羹”的心声。此外,姜埰还与沈泌同登宣城卧佛阁,礼佛参详;访梅磊位于翠微峰的响山草堂,姜埰以“宣州老兵”为荣。 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苏州艺圃的姜埰在弥留易箦之际,嘱咐儿子“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丘首,吾当待尽宣州,以终吾志”,将吾葬于敬亭山下。其子姜安节尊父命扶灵归宣,在敬亭山结庐守墓最达十二年之久。姜埰其心其志其节,令宣城人民动容,他是真正的不是宣州人的宣州人。

由于姜埰、姜安节父子在宣城的种种作为与经历,他们对宣城的这种一往深情,对清早中期宣城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巨大,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深远,是人们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我们知道,宣城乃江左名郡,两千年来不仅人才辈出,且文人雅士宦迹宣城或慕名而来者如过江之鲫,宣城人将张慎言、姜埰入祠,表明宣城人的昭昭大义、是一种崇德向善的人文精神的宣示,使人们更加向往与热爱宣城。可惜,2009年11月的一场雪,将位于宣城敬亭山的先贤祠彻底摧毁了。
在古代,宣城不但有先贤祠,还建有乡贤祠。祠内镌刻本地乡贤的生平事迹,供人赡仰、学习与宣传,这好像我们今天的宣城好人馆一样。 宣州乡贤祠,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兴建,过了四十年,到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庙貌倾圯” ,当时宣州知州贵中孚有心愿说:早在“乾隆辛(1751年)未夏,余宰兹土,操刀初试,思欲寻古昔之衣冠,每当春秋瞻拜,望几筵而愿有以整茸之,时节因缘,志未逮。” (清•贵中孚《重修乡贤祠记》,下同) 当他正在为难时,正碰上章孝廉的后人章生春来宣州祭拜。章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很受感动,他说他愿意独自出资帮助重修此祠,贵中孚听了高兴至极,喜叹道:“余固喜得藉手以观厥成也。”果然,当年(乾隆二十一年即公元1756年,“爰畀之鸠工(就地石集工匠),于今夏仲(夏天的第二个月)落成”了。贵中孚在《重修乡贤祠记》中赞扬章生说: “今章生乃能嗣厥先志,虽无老成,尚有典型,夫亦在庙之灵爽所式凭焉者耶?是不可不记也。”贵中孚把章生的善举记录下来了,彰显他的高煮品情,立为楷模。

从明到清建的这乡贤祠,皆供奉着本地的乡贤,清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前,祠内有 “奉祀者主七十有九(79人)” ,这些人中: “有孝友者,有忠义者,有廉洁者,有鲠者者,有宗正学者,有优相业者,有勤吏事者,有敏训迪者,有文学者......” (明•邹守益《乡贤祠记》)也就是说,有各行各业的品行优秀者。据《宣城县志》载:明代就开始,时任宣城郡守的贡汝成曾写有《乡贤祠铭》,记录着乡贤祠中宣城的先贤,他说: “若我宣郡,固多名英。有焯其著,梅(尧臣) 贡(贡师泰) 汪(汪泽民) 陈(陈迪)。一代人物,百世法程。”尤其是忠贞不渝的汪泽民与浩气长存的陈迪,其忠义在后世倍受褒扬。

汪泽民(公元1273—1355年),字叔志。据《元史列传•第七十二》载:他“少警悟,家贫力学,既长,遂通诸经。延祐初,以《春秋》中乡贡,上礼部,下第,授宁国路儒学正。五年,遂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书愿夺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养。” 大学士和尚留之道:“集贤、翰林,实养 老尊贤之地,先生何为遽去?愿少留,以副上意。”汪泽民说:“以布衣叨荣三品,志愿足矣。”(《元史列传•第七十二》)遂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即退休)。时年已70多岁了,垂垂老矣。“公既归,筑室宛水之滨,读书自娱。”(《宣城县志•文艺志卷二十九》)。他居住在宣城城南,老年以读书为快乐。回来后,除侍奉老母外,与門生故人相来往,做诗填词,嬉游若忘世者,并自称“堪老真逸”。“湘中三年梦井乡,敬亭重游心目醒。双流夹镜一溪来,千仞齐云两峰并。” (《秋日同游敬亭》)“春日游戏日相关,带雨看花紫翠间。闲读唐碑访遗迹,石麟残缺补丁山。” (《游广教寺》)并致力于《宛陵遗稿》的写作。这么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做过贡献的人,退休以后过着这样清静、和平、自乐其得的日子,汪公真是在贻养天年了。然而,不久这平静的生活被当时的政治形势打破了。“至正十五年,(1355)蕲黄义军攻陷徽州;后犯宣州” (宋濂•《元史列传•第七十二》)是走,还是留,完全由汪公自由选择,因为他既无官衔,更无责任。然而汪公选择后者,并自告奋勇担任“东部使者,画守城,御寇之策十余事,寇兵至,击退已。(明•王恕•《汪文节公祠记》)。“江东廉访使道童雅重泽民,日就之询守御计,城得无虞。《元史列传•第七十二》,下同)” 更难能可贵的是:第二年“长枪叛帅琐南班、程述等渡江,欲犯宣城,” 形势更为紧张,严峻。“城中兵不满数百,或劝泽民避去,廉访使木八沙、周伯琦亦以为言,” “公曰:‘昔江万里,寓鄱阳大军逼城,众皆走散,犹坐守以为民望,况宣民离合,视吾去留夫何之?’”汪公和城中军民坚守城池,军费不足来“泽民从容一言,获钞万锭,米三千斛。八月,江浙行省参政吉尼哥儿遣兵来援,城中恃援至,守懈,贼乘夜攀堞以上。城陷。”汪公被叛军逮到后。逼他投降,他至死不降“将死骂犹不绝口,”,“遂遇害,年八十三。” 作者由此感叹道:“公当谢事归田之日,无职守、无责任,寇至而不去以为民望,复为部使者,画策以御之,及其被执逼降,至死不屈,此其所以难能也。” (明•王恕•《汪文节公祠记》,下同)因此死后被封为“资善大夫、江浙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为“谯国郡公”,给予的封号“文节公”。“文节”一词意为“无守土之责, 但取义成仁”,表现的是一种高风亮节,卓而不群的牺牲精神。”

陈迪,字景道,明洪武乙卯(1375)进士,顾命大臣,辅政五年适燕王兴兵,夺皇位辗战攻入南京,建文帝逃逸。燕王召陈迪问,他坚决不归新王,燕王称帝,将陈迪的两个儿子丹山,风山五马分尸。燕王命人割下陈迪身上的肉塞进他的嘴中,并问气味怎么样。陈迪回答说:“忠臣孝子的肉哪有膻味?我觉得肉味鲜美,别人能闻到香味,你难道没闻到吗?”遂一家六口,于南京市口被全部被杀害,他到死都不屈从,表现出一种忠君爱国的民族气节。
汪泽民、陈迪这些乡贤,明成化八年(1472年) 乡人把他的牌位和其它先贤一样供于乡贤祠中。在《乡贤祠记》作者还中叙述了宣城乡贤的历史渊源,说: “自晋孝廉何公琦至我朝董公杰,有孝友者,有忠义者,有廉洁者,有鲠直者,合三十人。”然而这些邹守益认为“相去甚远” ,必须有自已的乡贤祠。当时的宣州知州贵中孚说: “宣州,江南之胜区也,或出或入,代有闻人,岂以地而特秀与?然吾闻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荀贤者在焉,斯足以寿千古。”(宣城县志•卷之三十艺文记下) 他的意思说,宣州有这么多贤人,足足可以名垂千古,要树立自己的榜样,为什么不能建乡贤祠呢?故而他才有此决心与信心。

也许有人要问,宣城建的先贤祠和乡贤祠,供奉这些人到底起什么作用,邹守益说:它的作用是 “率耽情于丘壑之邃美,寄兴于风泉云树之幽奇,所谓千秋万岁魂魄犹应恋此者,故之敬亭云尔。”也可以“霭然可以励俗矣” ;从整个地区来说,宣城人民以这些人为标杆,倡导优良民风,提倡正能量, 所以宣城向来民风淳朴,“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笃亲者,章其忠义而俗知报主者,章其廉洁而不贪矣,章其鲠直而不诡随矣,章其正学而俗道术一矣,章其相业者而覆谏者惧矣,章其有吏事而素餐者惭矣,章其敏训迪而乐育者奋矣,章其文学而通经学古者出矣,兹区君所以风励郡人而诏之之志也。”建祠不但对地方有教化,对整个国家来说,“国家彰善瘅恶,以化民俗。”“宣上德意而正民俗者,且将百世有光矣。”基于这样的认识与效能,宣城历代地方的当政者都重视先贤祠与乡贤祠的兴建与修缮工作。从现在看来, 尊崇先贤,注重教化,成了宣城人民延绵不衰的优良传统。

由此,我想到,现在我们设的宣城好人馆,在馆中展现各行各业出现的好人事迹,不也是以他们为揩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社会正能量,倡导新风尚么,不是与过去先贤祠与乡贤祠提倡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么?这正如贡汝成在《乡贤祠铭) 中说: “道被天下,天下共享; 道尊一乡,一乡专仰。”所以说,昔日的先贤祠与乡贤祠、现在好人馆,真正作用与教化所在,它起着引导人们向善、走正道的作用,也增加了当地崇尚气节和儒雅的文化氛围。 “绵绵无绝期” ,文雅之风,刚烈之气,在我们宣城会代代流传,宣城如今成为全国文明城市,从这里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