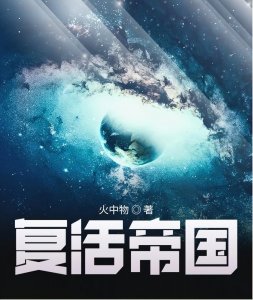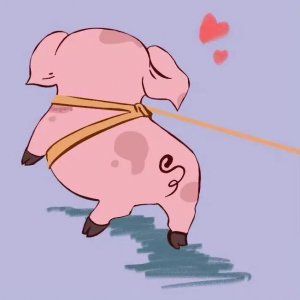贞洁牌坊,盗墓贼揭露出来的秘密
石匠的地位在老家地位很高,石匠也分三等,最低一等砌凿墓碑,中间一等砌凿石桥,最高一等砌凿的是牌坊。
而生意最好的就是最低一等的砌凿墓碑的石匠,砌凿墓碑,与家家户户有关系。
有丧事的主家很少讨价还价,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
不过,很多人知道这种石匠与盗墓贼有点往来。
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连隐藏的豁扣、活砖也一清二楚?
还不是石匠露了口风。

牌坊,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盗墓贼在乡间被称为“掘坟光棍”,在这里的“光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身,而是延伸出来的另一种意思:胆大、不在乎。
最厉害的掘坟光棍叫“夜仙”,而墓碑石匠叫做“夜仙班”,又简称“仙班”。
名声最好的是牌坊石匠,乡亲们都尊重他们。牌坊是让人们仰望的,他们也跟着让人抬头了,尽管他们总是十分清贫。
另外牌坊石匠的技术也是最棒的,需要工整,并且有艺术性。
牌坊石匠活儿少,立牌坊本身就是一个稀罕事,多年不遇。
与“状元牌坊”“御赐牌坊”不同的是,乡间的牌坊多是为女人立的“贞洁牌坊”,为一些已经亡故的女人,能够坚守“妇道”“贞洁”,守着公婆、儿女,清贫度日。
这些牌坊都在表彰这些女人“从一而终、寡而不嫁”的事迹,因此叫做“贞洁牌坊”。

现在的观点感觉这些可笑,可悲,什么从一而终,什么清贫而终!老娘可不伺候,这也是这个年代再也见不到的现象,就是有,也不会宣传,更不会立什么牌坊。
那时候,乡间的寡妇很多,能立牌坊的却是极少数,因为它需要一系列苛刻的标准。这标准不是基层“领导”能够决定的,他们只是负责上报,然后经过层层审批,甚至需要皇帝的御批。
比较起来,远近闻名的是“范夫人牌坊”最大。
这个范夫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其中有一个儿子参加科举,做了高官。
正是这个儿子,在母亲过世时报请,给母亲立了这座牌坊,立得相当考究。

牌坊是一种文化象征
其他那些牌坊,说起来有些怪异。比如,男女还没有结婚,未婚夫却死了。
按照古代风俗,两人根本没有见过面,可这未婚妻一听未婚夫去世,竟然自杀殉情,这也太拉风了!但是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或者未婚夫死翘翘后,女子守贞不再嫁人,家人为了女儿的幸福,就想让她另嫁,威逼女儿,女儿气不过,便悬梁自尽,这更拉风!
于是,便为这样的女子立牌坊,在史书上,史学家还专门为她们立传,称赞他们,叫做“烈女传”。
现在看来更是一些“糟粕”,封建糟粕。
但那时候不行。
牌坊作为一道风景线,是当地扬名立万的招牌,因为牌坊总是靠着大路,有宽大的石基可以坐卧,有石柱可以靠背。

闲的时候,百姓们喜欢来牌坊这里闲扯,农村除了农忙,基本都闲,况且那时候都不去打工。所以这里是农村集散地。
范夫人牌坊就有这种功能。
这天早上,村里德高望重的牌坊石匠潘木公出了家门上了大路。
他穿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衫,肩挎一条长包袱,手提凿石工具,不紧不慢地经过范夫人牌坊。
邻居问他哪里去,他说昨夜受到邀请,到山南镇去督建一座牌坊。
这可是一件大事,乡人们立即传开了,这是近几年来第一遭。
山南镇在十里之外,按照当地风俗,只要是大师傅,每天还要回家来住。
因此,傍晚时分,很多乡民挤在牌坊下,等他回来,打听蹊跷的事。
人群中,最兴奋的是一位年轻的“仙班”。
也就是很可能与掘坟光棍有勾结的墓碑石匠。
墓碑石匠与牌坊石匠向来交往不多,但这个石匠一直想拜潘木公为师。

毕竟牌坊石匠是一种高雅的工作,虽然没有自己墓碑石匠来得实惠,可人家牌坊石匠层次高,要是自己做了牌坊石匠,那档次可就不一样了。
以前曾托人捎过话,都没有回音。今天听说潘木公早上出门心情不错,就在牌坊下候着,看能不能套个近乎。
如果套上近乎了,就有一个萦绕在心头的疑问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疑问搁在心头已经很久了,对别人不能说,也不敢说。
夕阳西下,潘木公踉踉跄跄的身影转过山脚来的时候,看上去很累,与他早上出门时完全不同。
年轻石匠很早就迎了上去,接过他的包袱,搀着他在牌坊的基石上坐下。
潘木公感激地看了看年轻石匠,觉得有点眼熟。
年轻石匠说:“我也是石匠,没出息,做墓碑的。”
“你也是石匠?”潘木公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说,“明天跟着我去山南镇,那地方,连个帮手也没有。”
这是求之不得的,年轻石匠一听,光怕潘木公反悔,立即点头,说:“好,我跟着您,听您吩咐。”

在第二天去山南镇的路上,年轻石匠不断地找话与潘木公搭讪,最后,终于支支吾吾,把那个搁在心头的疑惑说了出来。
重点来了!
“木公,您平生所建的那么多牌坊,多数是小女子的吧?”
“唔。”潘木公素来言辞不多。
“那些可怜的小女子,我先给她们凿墓碑,您再给她们凿牌坊,也算是造化了。”
“造化?”潘木公反问了一声。
“我说是运气。”年轻石匠迟疑了一下,又说,“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她们就上天了。”
“上天?”潘木公摇了摇头,说,“牌坊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自杀就是自杀,都那么年轻,总叫人伤心。”
“但是,只要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墓就空了,真的飞走了。”年轻石匠说道。
潘木公猛地回过身来,捏住了年轻石匠的手,问:“什么?墓空了?你这么知道?”
墓碑石匠当然知道了!他和盗墓贼就是一伙的吗。
看着潘木公严厉的目光。这一下,年轻石匠慌了。

他每次完工后,确实有盗墓贼来威胁利诱,逼他说出墓葬情况。
但是,只要是立了牌坊的自杀女子,盗墓贼去了,每次都空手而归,因此总会把他恶骂一顿。
次数多了,年轻石匠就判断,那些女子全都升天了。
但这只是猜测,他很想从潘木公这里找到答案。毕竟潘木公是牌坊石匠,而那些不见了的女子,但是有牌坊的。
“你入伙盗墓了?”潘木公厉声逼问。
“没有,是夜仙班那帮掘坟光棍说的。”墓碑石匠赶忙辩解。
他看着潘木公疑惑的目光,干脆就把哪几个掘坟光棍分别挖了哪几个女子的坟墓,一一报了出来,态度十分诚恳。
“都是空的?”潘木公停下了步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自言自语。
说着他又抬头问年轻石匠:“落葬时,棺材肯定是放进去了?”
“我都在场,肯定是放进去了,家人哭得稀里哗啦。”
“棺材不是空的?”潘木公追问。

“那我怎么知道?但从抬的样子看,有分量。”墓碑石匠。
潘木公从腰束上掏出烟杆子,塞上烟,点火抽了起来。
好一会儿,潘木公断断续续地说:“我造牌坊时,也碰到过一些蹊跷事,一直想不通。……墓里是空的?怎么会?……道士说升天,是说魂,身体不会升。那坟墓里的身体哪里去了呢?……”
这是一个谜!
抽完烟,两人起身,向山南镇走去。他们又去建造一座新的牌坊。
故事出自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最终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可似乎又说出了答案。#头条品书团#
没有人去去验证,就是偶尔打开了这些立了贞洁牌坊女子的墓穴,也可能以自我暗示的借口来诠释这种形象。
但是盗墓贼不会,他们被这种现象感到迷惑,也因此感到震撼和恐惧。
历史、社会、世界、民间、官方、小道消息、史书记载、信仰传说,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秘密。
这些牵扯到灵魂层次的界面上的事,一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维度空间可能达不到,二是我们缺乏研究下去的胆略和能力。

不过在这个世间,史学家、一些信仰者,总会给我们半晦半明的点出一些现象,人的纯、真、正,都是有能量的,能在这个世界秉承“孝”、“诚”、“忠”、“仁”,等行为的至善之人,总会在冥冥之中得到昭示和实惠,这可能就是天心与人心的相合吧。
余秋雨说,《文化苦旅》就像是一个外出的浪子,而这个浪子带给他的麻烦是极度热销。
文化苦旅心的旅程
¥67.6
购买
这哪里是浪子吗?这明明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吗?
文化从来都不苦,它在就在那里不动不摇、不偏不倚,而看上去我们这些孜孜苛求的所谓文化人,才是“苦”的,被自以为是的文化所转、所蔽、所苦。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名、相,使我们放不下,逐名夺利,就变成了这个世界的常态。生活本不苦,苦的是我们被生活左右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