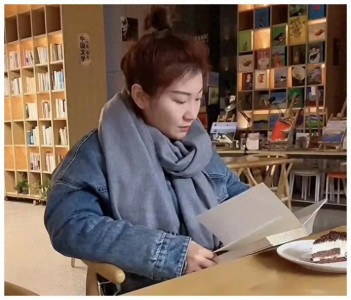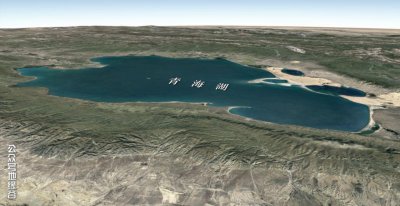ptsd是什么梗(“创伤”如何成为过去十年的流行语?)
参考消息网2月12日报道
美国沃克斯网站1月25日发表题为《“创伤”一词是如何成为这十年的流行语的》的文章,作者是莱克西·潘德尔。全文摘编如下:

2021年2月,巴塞尔·范德考克关于心理创伤的畅销书《身体从未忘记》跃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非虚构类榜单的榜首。那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第二年伊始。
《身体从未忘记》一书并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新书——它于2014年出版,在2017年进入了该榜单。尽管该书偶尔会被夺走榜首宝座,但它一直反复登顶。
“创伤”无处不在
创伤是真实的,而且可能导致真正的疾病,尽管其含义一直在不断发展。然而,一些进行创伤研究的人说,在当今文化中,人们提及这个词时变成了半开玩笑,随意的,还夹杂着对过去之事的认真忏悔和审问——对以前定义方面的误解,对过去发生的荒谬可笑的事、微不足道的事、影响深远的事和真诚的事。
图兰大学教授兼医生迈克尔·舍林加说:“‘创伤’一词可以意味着一切。我被堵在路上了:这带来了创伤。我的足球队输了:这带来了创伤。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就是这个词的用法。”舍林加即将出版《创伤带来的麻烦》一书。
“创伤”一词不是被简单地淡化处理了,而是被广泛地用作一种文化试金石。
媒体心理学家帕梅拉·拉特利奇说:“‘我有创伤,’这句话就像‘我很沮丧’或者‘我对饼干上瘾’。这已经成为一句流行的俗语,人们随时丢出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含义。”
虽然将我们对创伤日益浓厚的兴趣归咎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做法很有吸引力——当然,对许多人来说,疫情的确造成了创伤——但多年来“创伤”一词一直在我们嘴边。过去18年来,谷歌关于“创伤”一词的搜索结果数量稳步上升,在2021年达到了峰值。书籍也呈现出这一趋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提到创伤的书籍大量涌现。
几年前,墨尔本大学心理学家尼克·哈斯拉姆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这不仅仅是一种术语时尚。它反映了精神科医生和整个文化对这个词的词义的稳步扩展。滥用这个词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影响。”
过度拓展术语
作为一个术语,“创伤”一词模棱两可。它可以表示身体损伤、一段经历或对可怕事件的情绪反应。这个词源自希腊语中的“伤口”一词。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创伤”一词被用来指代心理伤害的用法才出现。
快进到一战,当时英国医生诊断士兵患有“炮弹休克”。范德考克在《身体从未忘记》一书中写道,尽管患者一开始得到了治疗并领取了残疾抚恤金,但此症最终被认定是“散漫的、不情愿的士兵”的性格缺陷。
当范德考克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与越南老兵合作时,他写道:“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图书馆里没有一本关于战争创伤的书……与此同时,公众对创伤的兴趣呈爆炸式增加。”
随着美国人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种族不平等、对妇女的暴力和虐待儿童开始被视为创伤。
到20世纪90年代,诸如“文化创伤”、“集体创伤”、“历史创伤”和“代际创伤”等用语开始变多,特别是在与种族灭绝、奴役和战争等问题相关时。
然而,这一术语的扩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康奈尔大学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科学家贾尼斯·惠特洛克说:“‘创伤’一词开始成为容易使用的说法,被用来描述心理健康挑战。”
“创伤”成为趋势
研究人员开始掌握创伤的概念。之后不久,全美就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爆点:创伤成为趋势。惠特洛克说:“创伤叙事变成了很容易采用的叙事,即使对于那些并未经历过我们所说的大量创伤的人来说。它有通用性,所以人们充当它的经纪人。”
大约15年前,惠特洛克开始听到人们用“创伤”一词来描述更具普遍性的、令人不安的经历。惠特洛克说:“我的一名研究对象专门谈到了她如何感知创伤的层次性。人们有种感觉,你的创伤越严重,你所面临的心理健康挑战就越有正当理由。”
舍林加还将2005年标记为一个转折点——在研究领域,对创伤开始有了颇具争议的新的理解。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指的是反复发生伤害性事件所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比如童年受到虐待。舍林加说,感觉自己的同事对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没有遵循证据”。
这项研究大多称,对受到创伤的患者进行了大脑扫描,扫描结果显示,大脑出现异常情况,包括负责评估危险的大脑部位杏仁核。然而,要真正了解创伤是否会改变大脑结构,纵向研究必须证明并不存在先前已有的神经生物学差异。舍林加认为,还需要做大量研究。
不管怎样,经历过困境的人接受了这种想法——或者他们只是被这种想法吸引来的。正如舍林加所说:“在个人层面上,患者称,‘我相信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它帮助了我,它为我解释清楚了很多事情’。”
重新定义“创伤”
一个事件是否会在造成伤害,具有破坏性,产生后果,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又不会造成创伤呢?一些专家谈到要区分开“大”创伤与“小”创伤,但这也许还不够。
范德考克不同意这一观点,即所有“创伤性”事件都会普遍造成创伤。正如他在《身体从未忘记》一书中所说的,2001年9月11日发生混乱时,他朋友的小儿子刚下车进学校。透过学校教室的窗户,能清楚看到双子塔和发生的一切。范德考克写道,这名男孩没有受到创伤。他的家人给予了支持。他把这一天融入了自己范围更大的人生故事中,以及更大的可能性中。
20年后,很多新闻标题暗示,我们正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大规模创伤。这种保持距离的隔离、不确定性和恐惧难道没有造成创伤吗?正如范德考克对《大西洋》月刊记者所说的:“当人们说这场疫情是一种集体创伤时,我要说,绝对不是。”
对舍林加来说,创伤绝对是一个单一的、意外的、危及性命的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然而,如今,正如像拉特利奇所说的那样,许多人改变了创伤的定义:“你理解世界的方式已经改变。”
通过依靠创伤来理解我们的现代生活,我们正在削弱压力和令人难以应对的事件所产生的真正影响。我们将所有的困境都扁平化,将可怕的和令人极度悲痛的事情与只是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混为一谈。哈斯拉姆写道:“使用‘创伤’这个词,会将每一个事件都变成灾难,让我们感到无助、崩溃和无法继续前行。”
我们倾向于将创伤泛化,这说明我们希望认识到人类经历的复杂性,这点值得称赞。惠特洛克说:“对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和了解人体如何运转来说,存在一个绝佳机会。”加强关于创伤的定义,并不会从我们可怕的个人经历、历史恐怖事件或在我们当前社会结构中的生存困境中抽离任何事物。这不会限制我们的共情能力,也不会削弱我们从悲剧、危机或挑战中恢复过来的必要性。这并没有忽视暴力和生存恐惧的真相——尽管它的确承认,可能会产生后果,但不一定存在创伤。
或许,正如舍林加所说,“我们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脆弱”。